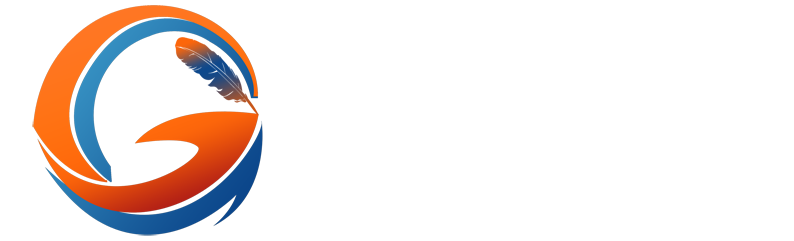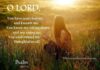作者:羅樂呈
1. 引言
利科採取的哲學詮釋學,以符號、象徵、隱喻和文本來理解人的存在與意義,提出「三重模仿理論」結連敍事與生活。[1] 相較於傳統的釋經手法,例如從經文細節觀察作歸納式研經或歸納命題式教義,利科的敍事詮釋更能幫助讀者落實「基督的模仿者」的步驟。本文將以耶穌的兇惡園戶比喻(太二十一33-46)作例子,剖釋利科的各種敍事詮釋理論,與傳統釋經不同地對聖經詮釋作出貢獻。
2. 經文背景
兇惡園戶的比喻出現於耶穌在受難週進耶路撒冷城後,在聖殿教訓人的時候被祭司長和長老質疑權柄(太二十一23-27)後,以三個比喻一併回應﹕兩個兒子的比喻(太二十一28-32)、兇惡園戶的比喻(太二十一33-46)和婚筵的比喻(太二十二1-14)。兇惡園戶的比喻同被記載於另外兩卷福音書(可十二1-12、路二十9-19),同是耶穌的權柄被質疑後作回應,唯只有馬太福音的記載是將三個比喻放在一處,是當耶穌對於猶太領袖指出神真正子民的問題時,以三個比喻來回應以加強效果,且作為耶穌在第二十四章預言聖殿被毀的重要鋪陳。[2]
3. 三重塑形
誠如上段理解經文的上下文和背景,傳統釋經一般透過分析經文結構、文法用字、對比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記載的不同細節、及當時的歷史文化等剖析經文,歸納命題式教義予讀者應用。利科的敍事理論卻提出模仿的概念,比傳統釋經更立體地將敍事世界連結於生活經驗。他延伸亞里士多德對模仿(下稱塑形)的理論,是一種具創造性的詩意建構的詮釋行為,按著敍事目標將事件排序成一個時間性整體的情節,把人類行為的因果配置嵌入情節中對應意義的添加,邀請讀者認同情節中的人物思想並以此敍述自己的人生。
利科提出三重塑形的理論,將敍事行動的敍事時間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重是「前塑形」,指進入敍事世界前對事情的預先理解,可以是倫理前設或民族關懷等個人生命狀態,遠超於傳統釋經所看有關經文背景的客觀資訊。第二重是「塑形」,指敍事者作出情節構建,將人類行動組織成一個歷時性的創造性綜合,為人物及事件賦予意義,帶著個人倫理法則配置成協調的故事,是受限於敍事者自身的前設。第三重則是「後塑形」,指按著對文本的理解重塑自身經驗,由受眾主導抉擇是否更新敍事身份和倫理身份宛如文本所述,且故事的終結不止息對讀者的影響,而是帶著「後塑形」成為新的「前塑形」,不斷進行三重塑形的敍事詮釋,帶來具創造性的互動。[3]
故此,應用利科的敍事詮釋理論進行釋經練習,是昇華了傳統釋經手法的細嚼文字,是在改寫現實生活中的對真理和對自我的理解,是為個人生命帶來啟發性的改變。以下將嘗試以三重塑形的理論,應用於兇惡園戶的比喻。
3.1 前塑形
這比喻的敍述者耶穌,在敍述之前是剛以君王身份進城和潔淨祂的聖殿,被設法捉拿祂的的猶太首領質疑權柄和設法陷害(太二十一23、46)。從祂說這三個比喻的結論(太二十一31-32、43、二十一14)可見,祂指責不信的猶太領袖和教導人進神的國而建構的敍述,是出於祂期望祂的子民回轉的前設。
比喻的受眾猶太領袖們,面對耶穌大行神蹟奇事而聲名大噪,一方面按他們既往對彌賽亞的期盼而拒絕承認耶穌的權柄,另一方面參考約翰福音(十一47-48),他們因耶穌流失了部分支持者而恐懼從羅馬政權中失去權勢,是帶著不容耶穌詆毀上帝救贖者的榮耀和猶太領袖權勢的前設進入聽比喻的敍事世界。
在耶穌說這比喻的時代,以葡萄園(太二十一33-41)和石頭(太二十一42-44)作比喻,是聽眾猶太人們所熟識的。先知書和詩篇多次以葡萄樹比喻以色列(結十五1-4、詩八十8、何十1等),最為熟悉是先知以賽亞的「葡萄園之歌」(賽五1-7)以葡萄園比喻以色列家,表達耶和華悉心培植的以色列卻違背神,將遭耶和華撤去保護的籬笆使其荒廢。另外,「匠人所棄的石頭」引用自詩篇一一八22-23,從祭司長和法利賽人聽見比喻後明白是指著他們說的(太二十一45),可見這敍事的前設與聽眾前塑形世界中民族文化對象徵的共同理解相符。
3.2 塑形之情節構建
敍事者選擇性帶著個人道德倫理前設進行情節構建,為故事中的人物及事件添上動機和原因來配置成一個協調的敍事。由於這個「葡萄園」的比喻跟神在歷史中不同階段和以色列民的互動都吻合,一般被理解成「寓言」故事﹕[4] 葡萄園是以色列、園主是耶和華、園戶是猶太領袖、一個接一個的僕人是歷代的先知、承受園主產業的兒子是神的兒子耶穌,這比喻有猶太領袖殺害彌賽亞的寓意。[5]
利科敍事神學看敍事的情節構建遠超於上述從經文對比零碎地分析比喻中各元素的含意來引伸寓意,他看這塑形的過程為敍事者刻意地為敍事中的每一個元素添上動機和原因,至少包含起初、發展和結局來形成一整體的故事,[6] 避免寓言化比喻以致輕看情節的發展,而是叫讀者投入文本投射出來的敍事世界。
故事中的主人翁葡萄園主起始的動機為收成果子,他為此沒直接租出空地等待收成而是悉心整地挖池蓋樓栽好葡萄園,且圈上籬笆好好保護葡萄園的果子。園主信任人和明白事理,他信任園戶承租亦信任僕人去收果子,且到收果子的時候才去收取。被園主差去收果子的僕人是忠心順服的,即使前面被差去的僕人遇害,仍順服主人差遣去犧牲受苦。至於園戶的動機是要佔園主的產業,他們刻意拿住園主的僕人施害,不但不按時繳租,更拒絕承認園主在葡萄園的主權,甚至殺害承受產業的園主兒子來意圖把葡萄園據為己有。故事的發展隨著一個接一個被差去收果子的僕人被殺害,至故事高潮園戶把園主的兒子推出葡萄園外殺掉。故事的轉折點在耶穌反問聽眾在園主回來時該如何處置兇惡的園戶,而聽道的人回答說要除滅兇惡的園戶另租給按時交果子的園戶,解決故事中園主與園戶之間的衝突。耶穌另以「匠人所棄的石頭」帶出故事的主要訊息,比喻以色列的兇惡園戶如此殺害比喻耶穌基督的園戶兒子,終將被比喻耶穌基督的房角石審判,被奪去神的國作為故事的結局,以整個情節結構組成敍事時間線和刻畫人物動機,作為敍事者耶穌的敍事身份。
3.3 塑形之極限經驗
利科形容比喻為敍事形式和隱喻過程的結合,產生一種極限體驗,即按前塑形世界的真實傳統作敍事中加插反常的情節,使聽眾原有的存在價值觀被衝擊,開拓讀者詮釋的可能性,從而重塑其神學和道德觀念。[7] 這兇惡園戶的比喻按聽眾熟悉的葡萄園作敍事背景,是任何猶太人都能意識到園主是比喻耶和華,來宣講以色列民與耶和華的關係。在這平凡和貼近聽眾現實世界的人性寫實故事中加入不合理的情節,即園主明知道園戶一個接一個的殺害他差去的僕人,還進一步差自己的兒子去收取果子最終連承受產業的兒子都遇害。參考同樣記載兇惡園戶比喻的路加福音(二十16),當聽眾聽見耶穌說到園主要除滅園戶且將葡萄園轉交別人,象徵耶和華要除滅以色列且將神的國轉交別人,聽眾回應說這是萬不可的,反映這敍事世界對他們帶來的塑形與前塑形產生敍事角力。這聽眾回應的情感反映聽眾對情節的合理反應,是塑造價值和德性的過程,催促聽眾尋找隱含的行動樣式來解釋故事的離奇發展;同時亦叫聽眾看見另類的存在方式,引發對存在的反思,重塑敍述自己生命的方式。當結合尋常與不尋常情節的敍事世界粉碎聽眾的屬世價值觀,揭開深層的屬靈視野使其看見上帝的國,即前塑形與塑形需發生衝突帶來一種新的敍事眼界,才能產生後塑形。
3.4 後塑形
後塑形是當聽眾帶著自身的倫理前設,進入文本主導的敍事世界隨劇情發展走到最後一幕,站在敍事者觀點回望故事線上敍事者賦予各事件的意義,然後回到現實世界更新敍事身份和倫理身份的狀態。利科提出身份分為「同一」和「自我」兩種身份﹕「同一」(idem)是指靜態素材之間沉積而成的持續和穩定的人格主導著自我理解,而「自我」(ipse)是指一個隨時間遇上不同敍事角力可選擇改變的動態自我性主體,不斷在「同一」和「自我」之間對話達致歸一以形成敍事身份。[8]
兇惡園戶比喻的聽眾猶太領袖們既期盼他們心目中的彌賽亞出現,又希望在社會上鞏固從羅馬政權而來的權勢,帶著這些倫理身份前設,聽畢這比喻經歷過敍事世界帶來的極限體驗而產生敍事角力後,在深明比喻是指著他們(太二十一45),勸他們不要殺害神所命定的房角石、園主的兒子耶穌基督。經過前塑形與敍事的塑形之間的對立,本應使他們經歷質疑自己慣常做法,繼而啟發轉變並產生一種新的敍事眼界。最後他們雖然有更新自己敍事身份的可能性,卻仍選擇以沉積成慣性「同一」(idem) 的身份來拒絕故事邀請他們帶來更新,貫徹原有的倫理身份繼續找機會陷害和捉拿耶穌(太二十一46、二十二15),來保持自己的勢力,這敍事塑形使他們新的敍事眼界,因著害怕百姓和耶穌而更努力設法捉拿耶穌,以此成為進入下一次塑形的前設。
後塑形亦可應用於聖經讀者,按原有對神的國的認識作為前設,當進入敍事世界發現上帝差遣一個又一個僕人去收取果子後,不合理地差自己的兒子讓兇惡的園戶殺害,打破原有的觀念而發現上帝的國有如此的愛和忍耐,更新作為基督跟從者的倫理身份,理當相信承受產業的園主兒子耶穌基督並忠心按時交果子。這樣經過生命深化後,心悅誠服地內化外在之物來挪用新的敍事眼界,這倫理身份叫讀者甘願被約束於這敍事世界塑造的敍事目標,叫讀者超越執行聖經中教義式的命令而向自己的倫理身份問責,堅持對倫理身份的承諾,是一種實用性智慧,是結合客觀理智與主觀信心的知識。
4. 語意的創新
學者提出隱喻是字詞在特定處境下可被理解的範圍內創新地應用,字面上矛盾卻不至阻礙在思想和語言上的啟發與擴展聽者對世界的認知。[9] 耶穌在兇惡園戶的比喻中直接以石頭指出他﹕被匠人所棄、作了房角頭塊石頭、使掉落在他身上的人跌碎、和使人被砸得稀爛。固然在字面意義上耶穌並不是一塊石頭,且在比喻中沒有足夠的概念來解釋這種比較,但根據當時聽眾的文化代入能力,熟悉先知書中以石頭表示審判的標準(賽八14-15、但二34-35),語意的創新把兩件不相關的事物滿有張力地卻又可理解地劃上等號,使之掙脫字面的意義而創出豐富又複雜的新喻義,超出日常生活範圍的認知而豐富聽眾對世界的理解。
這是由於以地上片面的語言來類比上帝都不能精確代表上帝,在有限和語境化經驗的人類語言中,唯有以隱喻和象徵的豐富性來探索和表達神聖和奧秘。耶穌的比喻以敍事方式延伸隱喻的過程來指向上帝的國,以揭示上帝的作為來重塑讀者的身份。即使上帝並沒有出現於比喻的敍事中,隱喻最終卻指涉著上帝的國。透過這種非直接的溝通,超越傳統教義式說教的勸勉,令幫助讀者更易接受道理。
5. 「距離化」(Distanciation) 的理解
從耶穌這引用詩篇和先知書的敍述行動來理解兇惡園戶的比喻,耶穌在敍述的時間點與文本有一定距離,帶著敍述時聽眾的關懷對文本作出詮釋,才能達致詮釋的目標。被引用的文本的作者原所指的事物,已在耶穌說這比喻時的世界不存在,唯當文本原本的指向性消逝,才能解放敍述者的詮釋,按敍述時的生命狀態和對文本距離的自我理解,來賦予詮釋文本的意義。[10] 例如耶穌引用先知以賽亞的「葡萄園之歌」作比喻的背景,即耶和華對不結好葡萄的葡萄園顯明神對善惡的報應,形成敍述兇惡園戶比喻開始時與聽眾猶太領袖們的敍事一致產生共鳴。當進入這比喻的敍述,加上園主僕人和兒子被園戶殺害的不尋常情節,在距離化的文本詮釋添上顯明神對惡人的容忍和慈悲的道理,透過耶穌的詮釋為聽眾帶來新視野,轉化成叫猶太領袖們在拒絕接受耶穌和棄絕殺害祂的敍事前設以外,還有神對他們的慈悲和容忍,指出再不轉回向神的人,最終必受主的審判和刑罰的敍事。
這樣,同一文本被不同人引用來連結傳統作敍事,都會按敍述者特定的時空關懷作出不同情節構建的創新性,作出傳統與創新趨一的敍事。相較於傳統釋經看整本聖經為靜態啟示性的永恆真理,利科提出的距離化理解使聖經意義永不歇息。從耶穌引用「匠人所棄的石頭,已作了房角的頭塊石頭」(詩一一八22),到彼得引用同一處經文(彼前二7),甚至到今天牧者引用同一節經文進行宣講,都可按敍事時的特定關懷作出不同的敍述,即或詩篇一一八篇22節所寫的「匠人所棄的石頭」不含預言的成份,耶穌亦能以此喻作自己將帶來的審判,可見任何事件都能在往後有更多剩餘意義。[11] 上帝的啟示亦是漸進的,在讀者重讀聖經時,亦不減被經文塑造的力量,帶著第一次讀經文所更新的敍事眼界,連同已認知敍事者的倫理觀,再進入敍事世界的每一個情節中,再思自己現實世界中的敍事身份會否如劇本所述的倫理身份,生命不斷被經文塑造。
6. 結語
綜合以上利科的敍事詮釋理論,豐富了傳統釋經方法,從三重塑形中蘊含的敍事、隱喻、極限體驗、文本理解等以耶穌作兇惡園戶的比喻為例子,把詮釋學緊扣於更新敍述者和讀者的敍事身份。這不斷透過讀經敍事被塑造的信仰,就是始於潛藏心底的上帝觀,確信著上帝公義的引導下,在自我質疑和肯定的循環過程中不斷構建自己的敍事身份,不斷在真理中與實踐並行的成長。
參考書目
- 法蘭士著。沈允譯。〈馬太福音〉。《丁道爾新約聖經註釋 》。台北﹕校園書房出版社,2010。
- 莊雅棠。〈模仿自然,虛擬實境與效法基督〉。《神學與教會》第46卷2期(2022年1月),頁22-47。
- Contini, Annamaria. “Metaphor, between semantic innovation and conceptual transfer.” Paper for workshop. Moden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Modena and Reggio Emilia, 22 November 2013.
- Dornisch, Loretta. “Ricoeur’s Theory of Mimesis: Implications for Literature and Theology.” Literature and theology 3.3 (Nov. 1989): 308-318.
- Elwell, Walter A. Matthew. Baker Commentary on the Bible.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95.
- Gorospe, Athena E.. Narrative and Identity: An Ethical Reading of Exodus 4.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7.
- Keane, Niall, and Chris Lawn, ed.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hermeneutics. West Sussex: John Wiley & Sons, 2016.
- Mayward, Joel. “The Fantastic of the Everyday: Re-Forming Definitions of Cinematic Parables with Paul Ricoeur.”Horizons 47.2 (Dec. 2020): 283-314.
- Ricoeur, Paul. The Hermeneutical Function of Distanciation.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 Essays on Language, A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Edited by John B. Thomp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93–106.
[1] 莊雅棠﹕〈模仿自然,虛擬實境與效法基督〉《神學與教會》第46卷2期(2022年1月),頁30, 44。
[2] 法蘭士著,沈允譯﹕〈馬太福音〉《丁道爾新約聖經註釋 》(台北﹕校園書房出版社,2010),頁344。
[3] Loretta Dornisch, “Ricoeur’s Theory of Mimesis: Implications for Literature and Theology,” Literature and theology 3.3 (Nov. 1989): 308-314.
[4] 法蘭士著,沈允譯﹕〈馬太福音〉《丁道爾新約聖經註釋 》,頁345。
[5] Walter A. Elwell, Matthew, Baker Commentary on the Bible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95), 748.
[6] Niall Keane and Chris Lawn, ed,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hermeneutics (West Sussex: John Wiley & Sons, 2016), 174.
[7] Joel Mayward, “The Fantastic of the Everyday: Re-Forming Definitions of Cinematic Parables with Paul Ricoeur,” Horizons 47.2 (Dec. 2020): 289-292.
[8] Athena E. Gorospe, Narrative and Identity: An Ethical Reading of Exodus 4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7), 49-52.
[9] Annamaria Contini, “Metaphor, between semantic innovation and conceptual transfer,” paper for workshop (Moden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Modena and Reggio Emilia, 22 November 2013).
[10] Paul Ricoeur, The Hermeneutical Function of Distanciation,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 Essays on Language, A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Ed. John B. Thomp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93–106.
[11] Gorospe, Narrative and Identity: An Ethical Reading of Exodus 4, 17.
大家好,我是葉應霖。英文名是 Scott。希望您藉著呢個網更深認識神,別人及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