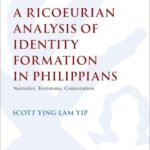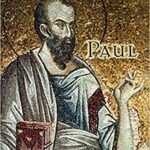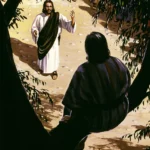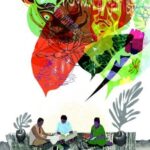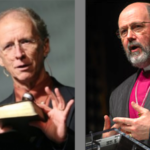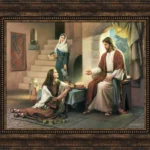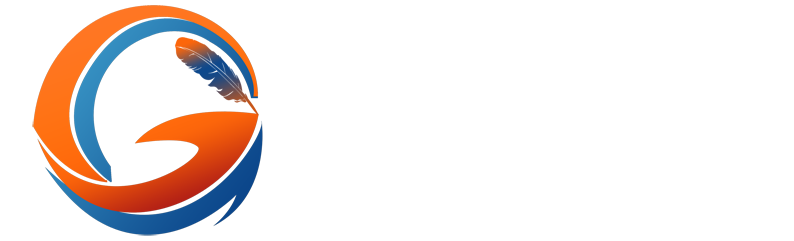用 200 個字總結我呢本嘔心瀝血的書(唔係用 ChatGPT 寫的)
Scott Ying Lam Yip presents the first specialised narrative study devoted to the identity formation processes in Philippians, based on Paul Ricoeur's...
超越「科學」的框框,走進「想像」的信仰
這是一個「故事革命時代」。當故事不斷被改寫,「自我認同」(self-understanding) 亦不斷被改變。無論是去年開始的社會運動,或是近期的新冠肺炎,兩者帶來的影響都是劃時代,影響著全香港及全世界。社會運動追求的新時代,是一種唯藉民主自由才能有的榮光時代。新冠肺炎帶來的,則是一種「世界末日」式的灰暗時代。相比之下,前者或者能夠為一部份人帶來「新天新地」的盼望,後者卻為大部份人帶來憂鬱的前景。前者叫不少香港人急忙「著草」,後者卻叫我們怱怱「回龜」。香港人呀,我們是誰?Who are we?
四角賽(2):傳統保羅:「我是基督徒,不再是猶太人! 」
一般來說,在廿世紀以先,更正教視信主後的保羅,為一位跟「猶太教」割席的基督使徒。未信主的保羅,就如當時的猶太人一樣,是靠自己的努力及好行為,嘗試去到換取救恩,亦即是所謂「律法主義」(legalistic Judaism)。好明顯,這些猶太人一定是徒勞無功,是全然失敗的。這些猶太人的心境,有兩個可能的特徵。一方面,某些人成功地自欺,以為自己已經達到上主的標準,自以為義 (self righteous)。另一方面,某些人不斷被自己的良心責備,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根本是有罪的人,不能滿足上主聖潔的要求,並非無可指摘(羅七18,腓三6)。保羅在未歸主之前,就是面對這樣的困境。外邦人,雖然沒有摩西律法,但他們與跟猶太人的問題,沒有兩樣。根據以上角度,保羅神學的核心,就是被良心責備的人,如何在法庭的場景,在那位聖潔的法官面前,得蒙赦免,被判無罪,亦是稱義的意思。
從「尋找罐頭式答案」到「被打碎及重建的敘事」:利科詮釋為我讀經靈修帶來的反思
作者:某同學
當我完成了有關保羅.利科的敘事理論的有關課程。使我回想我讀經的故事而且幫我整合有關經驗。 以往我讀經時,心態是想找答案。 我認信聖經是神的話,我可以找「最好」答案的來源。 就如拍拉圖對藝術品的看法: 有一個天上的一個「理想」答案。 當然,這一個較「理想」的答案出現了,我就要嘗試更理解神的心意。 但本於 「已經但尚未」(英語:already but not yet),所以即使聖經有一個完美的標準,現時的我是不能做到的,這合理化了我和聖經的距離。以下是一個例子,我是如何讀經及思考經文怎樣影響自己。
在約翰福音10:10,耶穌說,“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我的著眼點在於解釋豐盛。是如何靠耶穌得著這豐盛的生命呢? 沒有耶穌進來我生命之前,我生命的光景是否真的被毀壞呢?這經文也是我以往教會會堂放在門口的招牌上,作用就像以豐盛的生命叫途人想一想你的生命如何呢? 你想得到耶穌嗎? 而這經文對我就像指引燈一般:我想得到這豐盛的生命,就等於人生的完美標準一樣。但這年復年,我發現有耶穌的生命並沒有這麼豐盛,甚至有疲憊燒完(英語:burn out)的生命狀態,對於聖經指向的生命和自己的生命不一致的結果,我試著尋找答案。以下是我理性的整理:
一套令我流淚的「科研」電影:《居禮夫人:一代科研傳奇》
居禮夫人,一個自小我就聽聞的人物名字。電影《居禮夫人:一代科研傳奇》(Radioactive)的劇情一直有個伏筆,就是居禮夫人對死亡的恐懼。她不畏男性主導的學者群,不畏艱苦的研究工作,甚至不畏別人對她道德生活上的眼光。她參透放射性子粒的特質,參透當代科學的限制,其聰明智慧之高,令她成為歷史裡唯一一位能在兩個不同範疇上,獨得諾貝爾獎的女性。她的科研成果,其影響力可謂近乎愛因斯坦級數。然而,她一直不能參透母親死去的意義。死亡是什麼?母親在那裡?她想不透。
四角賽(3):大戰前夕––– 「新觀保羅」,傳統派的「敵人」來了!
在華人教會,「新觀派」一直不太受歡迎,評價毀多於譽。究竟「新觀派」是什麼東西?「保羅新觀」與我們的信仰經驗,又有什麼關係?今天就讓我用「我是好有猶太文化的基督徒」的角度,去演繹一下這個保羅。
利科思想對詮釋撒該的貢獻
傳統神學提供系統性反思,而且提供教義的內容及使信徒明白上帝不變的本質,多以慨念性及理性的思考式方式理解聖經和世界。 但現今世代,已經不可以單單以理性思辯認識世界,不同的社交媒體提供不同的記者視覺把事實以第一人的角度陳列在人前。後現代對世界對自己的理解已經是更複雜多變,不同媒界提供的浸沉式體現使人理解的事實是整合了理性,感情,客觀,主觀的體驗。敍事思想把我們日常的故事和神聖的故事放在時間裡,當我們把過去的事每一次重新被敍述,就是把我們所重整事件中的時間性結構, 這樣我們會把舊和新的敍事重新疊建,於是就可以改寫了我的敍事身份。就如,筆者去了一次很長的歐洲旅行,和朋友因不能好好配合,當下心情低落,但總算完成了旅程,筆者覺得不被接納,回到香港後大哭一場。當筆者再一張張照片放在社交媒體時,有著重新把旅程再回想一次的機會,述說著所見所聞,和重新整理旅行後和朋友的關係,重新敍述這個事件時,筆者和之前和朋友發生的事情等等疊建,使筆者明白了自己的性格,對方有可能對自己的看法,同時重新認識這朋友的性格,以及這個旅程使自己明白看事物的觀點,和不同人交流時的重心。筆者因這事對自己的認識立體了,這次對自己的認識是從痛苦而來,郤更深明白自己是個怎樣的人。如保羅.利科(下文簡稱利科) 提出當時間以敘事的方式被說出,它就變成⼈的時間,當敘事成為⼀種時間存在的條件,它便獲得了其全部的意義。當利科提及時間內 (Within-time-ness) 時, 便把人類所關心的事和敘述及時間關聯起來: 我對時間性的描述是依賴於我們對所關心的事物的描述。當筆者把旅行故事再次一幕幕敘述出來時,同時把時間/經驗的體會用語言顯露出來,成了當時/敘述時/對未來的我存在意義的創造。 這樣的體驗沒有離開事實,但不單單純理性,也反映著事件主角對特定時空下的關懷。 而這敍事思想很切合現今世代的經驗,當加以整合,幫助了自我身份的改寫。
豈能只是 OIA 2.0: 「起底」經文,「起底」自己
差唔多卅年前,初信主的我就參加教會的 OIA 歸納性查經班。作為一個初信者,跟著導師去 O 完 再 I 跟著 A,都真係學到野,增進了不少《聖經》的知識。但唔知點解,這種讀經及釋經方法總是給我一種「硬蹦蹦」的感覺。閱讀《聖經》的認知模式,亦跟我日常生活的方式,有點格格不入的感覺。
後來,我認識了敘事神學,才發現詮釋經文的關鍵,不單是歷史文法字義 (historical grammatical lexical),還有是經文潛藏的故事前設 (narrative substructure)。簡單來說,就是任何人的說話、報導或文章,其實背後都有一個以「故事模式」存在的「底牌」,去主導表面可見的邏輯。
歷史文法字義的查經步驟,嘗試客觀抽離地觀察一段經文...
四角賽 (4):「傳統」大戰「新觀」的死局
比較以上兩位「保羅」,「傳統派」的著重上主與人「縱向」 (vertical) 的關係,「新觀派」的則偏重群體之間「橫向」 (horizontal) 的。不難想像的是,當「新觀派」向著「傳統派」「橫衝」過來時,雙方對彼此的觀感,都會變得敵意。當「新觀派」重寫保羅的身分,和他所面對的的猶太教困境時,整個更正教的信仰核心,的確有被動搖的危機。在不少「傳統派」的學者眼中,將「基督的義」歸算人 (the imputation of Christ’s righteousness),根本就是人在神面前稱義的唯一邏輯基礎。在他們眼中,「新觀派」的觀點其實一點也不新,因為他們只是在重滔伯拉糾及中世紀天主教的覆辙。在另一邊廂,「新觀派」的學者就近乎一致地視「傳統派」將中世紀天主教的故事,讀進保羅的猶太處境。一言以蔽之,一個兩派互不相讓的死局。
豈只是負面教材?從利科 (Ricoeur) 的「極限經驗」重看路十38~42的馬大
本文旨在透過路十38-42有關耶穌到馬大家中的經文作例子,以展示保羅.利科 (Paul Ricoeur) 敘事詮釋學中部份思想對聖經詮釋的貢獻。本文的命題為利科的詮釋理論有助讀者突破既有教會教導並更深入和立體地閱讀聖經,並與讀者的「今天」和生命連結及互為更新。本文的進路大致為:首先審視教會一般對路十38-42經文裏馬大的看法,及後嘗試以三重塑形理論和其他利科敘事詮釋理論審視經文,以突顯學者在聖經詮釋上的貢獻和為讀者帶來的幫助。